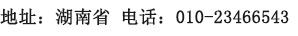梗概:少女时代的白荷花,人如其名:洁白无暇、叶绿花鲜。
白荷花随父学画,先学花鸟,后工人物。
白荷花画男裸体画跳灭灯舞,先后与一百五十五个半男人有两性关系。号称“古城第一妓”。
风流画家白荷花有一套惊世骇俗的绘画理论和新潮的性观念。
法院以流氓罪、强奸罪、制作淫画罪判处白荷花死刑。白荷花流氓集团案惊动了高层:死刑先后两次暂停执行。
作者描写了一个风流女画家多彩多维的人生轨迹,展示了一个女囚三次面对死亡的复杂心态:潜意识、躁狂、抑郁、偏执,失望、悲观、绝望、宣泄、恐惧、懊悔和幻觉、幻想、幻嗅及噩梦。
本书的语言如行云流水。
中国文学史上,以“风流女画家”为主人公的小说鲜有先例。文学人物森林里又多了一棵奇崛狂怪的红豆杉。
72.寄往阴间的信
荷花大姐:
你好!
提起笔来,不知从何说起。
每年四月二十四日,我和田苗还有闻思捷都来净虚县祭奠你。每年阴历十月一日,我们都要给你烧几件纸衣。
我从小害角膜炎,镇上的老中医胡坤楚说是火毒炽盛症,眼疼、口渴、便秘,眼睛老是红的。吃的中药能装几麻袋,仍没治好。考大学时,因视力过差,按成绩可以上名牌大学的我只上了个紫云师范大学。大学期间,我成绩优异,在校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小说、散文。毕业时,跳出教育界,当了一名记者。正当我春风得意欲大展鸿图时,角膜炎又发作了:角膜溃疡并迅速坏死,伸手不见五指。
当闻思捷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时,我不太情愿,说:“我不想长一双流氓眼。”
当时,你的影响太大了,我有那样的想法也不奇怪。老闻还有主治大夫反复做工作,我才同意了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,我太幼稚啦!
医生揭开蒙在眼睛上的纱布那一刻,我看见蓝亮蓝亮的窗帘,心里那个高兴呀,没法形容,眼前从来就没那么明亮过。白大姐,你是我的恩人,也是我的亲人。
大夫端来一个瓶子,里头用药水泡着我的角膜,已成羊脂状。
你离开人世已整整十五年。这十五年中,不仅中国变了个模样,整个世界也变了个模样。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,中国收回香港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,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。
烟州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摩天大楼一栋又一栋,但它与上海市比起来,至少落后二十年。
如今的古城内,到处是舞厅,跳二步舞、灭灯舞像撒尿一样平常。桂林路有个“红狐狸夜总会”,里头有小姐(当代妓女,又称性工作者)上百位。每天晚上,老板的纯收入三万余元(你在世时的一元钱相当于如今的十元钱)。那些小姐的收入就更可观了,陪睡一夜五百元小费,一个个都成了富婆,腰挂BP机,手提大哥大。这两样东西你没见过,顺便给你介绍一下。BP机是一种寻人的工具,纸烟盒大小,挂在腰间。我要找田苗,打个电话给传呼台,报上我的电话号码和田苗BP机号码,田苗腰间的BP机就“吱吱”叫了。她一看机子上显示的电话号码,就会给我回电话。丈夫腰里若挂BP机,便会被妻子控制起来,有事无事一天呼三遍,故,BP机又叫“电子拴狗器。”大哥大又叫手提电话,比BP机窄长一些。一拨号码,全球通。前些年,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才用得起,一部三四万元哩。如今不仅小姐用,连骑自行车的也拿个大哥大。这些小姐吃生猛海鲜穿狐狸皮大衣,戴钻石戒指(一枚上万元)和狗缰绳一样粗的金手链(一条也是上万元)。
去年夏天,烟州城来了十六位俄罗斯妓女,一个个丰乳肥臀。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,这些俄罗斯女人在“红狐狸夜总会”表演脱衣舞。音响里播放着男女交欢时的声音,俄罗斯小姐边舞边脱,时不时扭到客人跟前,用大奶蹭男士的脸或光屁股坐在看客的怀里。色男人又捏又拧又亲,淫笑声能震塌几十里之外山区小学的危房。收费也惊人:入场费一百元,一杯茶三十元,一包瓜子二十元。想看一场,不扔下二百元,你别想走人。一位二流作家酒后用湖南腔儿对我说:“老哥嫖的是俄罗斯小姐,长的是中国人的志气。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!”
前年秋,一帮子泰国人妖来烟州表演。人妖是男人,从小吃雌性激素,长大后,一个个酥胸翘臀,媚眼生春,腰似荷茎迎风。价也高得吓人:二百八十八元一张门票。想与人妖合影也成,一次一百元。
泰国人妖走后不久,一小队从泰国学艺归来的新潮中国妓女又在古城粉墨登场了。我去看过一次,让人瞠目结舌:她们会用玉门吸烟,五分钟内吸完一整根;她们能用玉门启开啤酒瓶盖儿,还会用下身喝啤酒,十几分钟喝一整瓶;她们把十几枚大头针塞入下体,然后一根一根给你摸出来;她们把三个鸡蛋塞进玉门,暖热后,“噗噗噗”吐给你。我见过一个东北姑娘,会用玉穴写字。她先把宣纸铺在小方桌上,再把大号提斗塞入下体,饱蘸浓墨,半蹲着写了个龙飞凤舞。这位东北姑娘还能从下身掏出鸟来:脱光衣服上场,半蹲着从丹穴里拉出来一大堆彩色绳子,拉着拉着,拉出一只五彩小鸟来,满场子乱飞。还有比东北姑娘更艺的:在另一家夜总会,我见过一位水灵灵的湘妹子从丹穴里“生”出一玻璃缸金鱼来,个个摇头摆尾,游来游去。
去之前,曾听同行们说过,我怎么也不相信。到那儿一看,妈呀,大千世界无奇不有!
这是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,没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,你提着猪头还寻不着庙门哩。
多少钱?入场费六百六十六元,瓜果、茶、饮料等共计九十九元。看客们若想包夜,每位每夜八百八十八元,一分不能少,也不多收你半厘。
卖身的地方很多,听我给你一一介绍:
发廊:理发、美容带按摩的。全身按摩每小时五十元。小姐们用脚给你踩背,每小时二十元。如果要保健——这是一句黑话,意思是云雨,一次一百元。现在,想在古城里找一家正儿八经的理发店太难啦!
桑拿澡堂:一种你想不到的洗澡法。把客人关在一间小木屋里,里头放一盆木炭火。你用瓢舀凉水浇上去,蒸汽充满木屋,像蒸笼一样,然后再搓再冲。没有小姐陪洗,每次三十元左右。如果有小姐搓背,加一百元。如果要保健,再加一百元。白大姐,你看吓人不?
卡拉OK厅:九十年代初从日本传过来的。给VCD——类似于你在世时的放像机里搭上碟片——类似于当时的唱片,与之相连的电视机里便会出现乐曲和画面,什么歌都有,你拿着话筒唱歌也行,跳舞也行。古城里到处是卡厅,夜半歌手们常用公驴一样的嗓子嗥叫,怀中的小姐则像母猫叫春一样唱着,聒得周围的群众不得不以棉花团塞耳才能入睡。卡厅里,小姐们陪你唱歌跳舞,也陪你睡觉,价格与发廊里差不多。人们称这些女人为卡拉妹。这几年,部分国营大中型企业不景气,下岗女工也有坐台当卡拉嫂的。
有人粗略地算了一下,仅烟州城就有一万余名小姐。她们每年从各邮局寄往外地的钱加起来超过三亿元人民币。
张力称这些小姐为“黄色娘子军。”她们是如何打扮的?头发染得像狐狸毛,眼圈涂得像挨了打,嘴唇抹得像猴屁股。
比起小姐来,女名模的形象更差:一个个骨瘦如柴,两腮无肉,似烟鬼像女巫,似白鹭像长腿蜘蛛。
烟州各大学校园均有自动售避孕套机。只要你塞进一元硬币,就会蹦出一个套子来。据烟州美术学院统计,平均每天售出二百多个,而全院仅有一千三百多名学生,其中女生占百分之四十一。
试婚的男女青年一天比一天多。去年冬,我采访一对在校外租房住的大学生时,眉清目秀的女孩毫不掩饰:“爷爷辈的婚姻模式是:结婚——同居——恋爱,父母辈的模式是:恋爱——结婚——同居,我们则是:恋爱——同居——结婚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这就好比挑西瓜,挑一个抱回家切开一看是生的就难换了。先尝尝对不对口味儿,对口味儿抱回家,不对口味儿就撇下。”我笑着说:“大家都这么尝这么挑,到时候满街道是尝过的烂西瓜。”
我在红狐狸夜总会见过几个当年坚决主张杀你的官员在欣赏脱衣舞。
杨甘劳早已离休,在家写革命回忆录。前年春,他在《老干部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毛主席送我一把枪》的文章。大概是他口述,儿子代笔的。文章发表后,被几家报刊转载。贺俊等老干部联名向中宣部告状,说是胡编的,姓杨的见没见过毛主席还两说哩。中宣部派专人下来调查,老杨傻了眼,承认是虚构的,又辩称:“我是在用小说来歌颂伟大领袖,有什么错?”
写到这里,你可能有些烦了吧?给你抄一首民谣,解解闷儿:
错位
警察横行乡里,参黑涉黄,越来越像流氓。
流氓各霸一方,敢作敢为,越来越像警察;
医生见死不救,草菅人命,越来越像杀手。
杀手出手麻利,不留后患,越来越像医生;
教授摇唇鼓舌,周游赚钱,越来越像商人。
商人频登讲台,著书立说,越来越像教授。
明星风情万种,见钱脱裤,越来越像妓女。
妓女楚楚动人,明码标价,越来越像明星;
谣言有根有据,基本属实,越来越像新闻;
新闻捕风捉影,夸大其词,越来越像谣言。
如今性病传播很快,街头的电线杆上、树上、公共厕所的墙上、报纸上、电视上尽是些治性病的广告。医院在广告中声称既能治性病又能修补和再造处女膜。医院更绝,能通过手术缝小阴道口,增加性爱快感。
世纪末,人们像疯了一样,一夜一夜打麻将,祖国一片麻将声。
前年春,我去日本时,一位叫尾崎士郎的记者对我说:“中国人就会发明一些玩的东西,奇技淫巧。要是在日本,发明麻将的人早已被杀头了。二战中,皇军是一只凶猛的狼。它挨了十几拳几十棒,又挨了炸弹和枪子。我认为:炸弹和枪子才是致命伤。”
世纪末的年轻人缺乏信仰。某老红军讲完爬雪山过草地吃牛皮带的故事后,年轻人大发感慨:“红军长征时吃的还是真皮带,现在到处是假冒伪劣产品,想找一条真牛皮带学红军煮着吃,难死啦!”
世纪末,造假已到了疯狂的程度:
硕大鲜亮的瓜果是因为喷了膨大剂和催红素;亮晶晶的大米是因为用“基础油”拌过。假蜂蜜是用白糖加香精、柠檬及食用胶熬成的;假冒的名牌火锅底料是用石蜡和畜禽饲料添加剂制成的;假醋是用化工原料冰醋酸勾兑而成的;假菜油是从泔水里炼出来的;假饼干中搀有工业用“基础油”,吃了可引起头痛、腹泻等中毒现象;假酒用工业酒精勾兑而成,喝了可致人死亡;胖油条中加有洗衣粉;肥鱼常吃主人撒的避孕药;阿胶用马皮熬成;夜市上的毛肚用福尔马林泡过;火锅里放有罂粟壳粉末儿……
洋人在中国办了许多工厂,雇用廉价劳动力,消耗低价资源,抽走大部分利润,扔下垃圾,排出废水。乡办化工厂和私营造纸厂的工业废水也排入大江小河,臭气熏天。鱼死了,河边的青草和庄稼枯萎了,沿岸的部分村庄成了“癌症村”。有的河水呈墨绿色,河里的螃蟹像李逵。用毛笔蘸着河水可以直接画山水画。捉上来一只螃蟹,无需动笔就是一幅现成的《水墨蟹》。
公款吃喝之风越刮越狂。天上飞的除了飞机,地上四条腿的除了板凳,海里游的除了军舰,什么都敢吃。菜名越起越怪:去皮黄瓜拍扁一凉拌,叫“玉女脱衣”;红烧青蛙称“花花公子”;炒土豆丝叫“斗私批修”;甲鱼汤称“牛鬼蛇神”;凉拌红、白萝卜条叫“小姐拉客”;三根薯条加两个剥了皮的熟鸡蛋称“三戏二奶”;给碟子上撒些白糖,放一堆西红柿条,美其名曰“西施踏雪”。乌龟王八、蝎子蜈蚣、白鹤孔雀、黄鼠狼金丝猴,什么珍稀吃什么。茅台、五粮液、人头马,什么名贵喝什么。
你在世时,医院治个感冒,只需花几元钱。如今呢?成百上千元。动个胆结石手术,原来只需二百余元。如今呢?近万元。你在世时,中学生每年的学杂费只有十几元钱。如今呢?上一所省级重点中学,仅赞助费就得交三万元,还不给你打收条。我上大学时,不仅不收学杂费,国家还给助学金哩。如今呢?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学杂费近万元。
中小学校用生产罐头的方法培养学生。学生们学到的要么是雕虫小技,要么是屠龙之术。
中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,作业越来越多,每人每天的休息时间平均超不过六个小时。《半夜鸡叫》中的高玉宝也比今日的中学生幸福。
你肯定要问:当年的办案人如今在干什么?这些人大多数升了官,有的还当了副局长、副检察长、副院长。也有混得背的,退休前还是个正科级助审员。退休的,多数干上了律师,夹着皮包出入各级法院。这些人呀,在任时极左,看谁都像罪犯,动不动就要砍头。退休后当上律师,又成了极右分子,明明该杀头,却进行无罪辩护。
我接触过其中大部分人,还采访过个别人。提起你的案子,都很不好意思。有的说:“当时就是那种形势嘛。上面叫严打哩,不杀一些不成。”有的说:“现在看来,那不算个什么案子。新《刑法》已把流氓罪分解为几个具体罪名。白荷花的案子,如果放到现在,只能定聚众淫乱罪,顶多判三五年。如果照当年的标准来杀,烟州城如今可杀的成千上万人。运动嘛,肯定得有牺牲品。”有的说:“白荷花检举的人太有背景,这是她走向刑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有一位老法官说:“白荷花长得非常出色。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那么美的女人。彭晓岗每回去看守所提审白荷花,面包车里都会坐满人。其他法官挤在车里干什么去?看白荷花。检察院和公安局的干警几乎都去看过白荷花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!说句心里话,当时多数人都觉得杀了可惜。那一天,我去了刑场,白荷花已经枯萎了。事后,群众议论纷纷,说政府把白荷花藏了起来,另找了个替死鬼。一九八四年元旦,我见过她一面,那时候的白荷花人如其名,真他妈的迷人!不到一年半工夫,怎么会蔫成那样呢?连我也不相信。”我去采访检察官雷积仓,他“嘿嘿”一笑,说:“白荷花真是一朵白荷花,谁愿意揉碎她?”我去采访彭晓岗,他摇头叹气,满面愧色。我问,他不答;再问,还是不答。
当年卷进流氓集团案的那些演员、导演、编剧和作家,如今大多数都成了腕儿(这也是个新名词,就是成了著名某某家),有人编的电影在国际上获了金奖,有人执导的电影轰动全国,有人的诗集流传到港台,有人成了大明星。名演员常到各地演出,出场费少则一两万,多则三五万。口袋里塞满了人民币,还要偷税漏税。腕儿们把出卖作品或演出挣来的钱用于旅游:天涯海角,欧洲非洲。开阔眼界后,绘画、摄影等作品在艺术上更有个性更成熟。他们在国外旅游或拍片时,免不了品尝洋女人。
当年“严打”时,因流氓罪入狱的女歌星边迪,九十年代初出狱后,唱了一首《囚歌》,红遍了北国南疆:
……
眼泪呀止不住地流,
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报纸大的牌子我脖子上挂呀,
大街小巷把我游。
手里呀捧着窝窝头,
菜里没有几滴油。
……
当年你检举的高干子弟中,个别人因案情重大被判了刑。法院判尤公子五年有期徒刑,宣判后不久,便保外就医了。
尤海轮如今是烟州市数一数二的阔老板,仅银行贷款就高达六亿多人民币。谁能把他怎么样?你去抓吧,抓了他才省心,贷款你去还吧。
去年冬,尤海轮来报社找我,说想登个广告。想看吗?顺手抄给你:
“西门庆男宝”武装他,一夜解放台湾岛
他叫秦无界,三年前因性无能与娇妻分手。今年秋,小秦服用大发明家尤海轮先生精心研制的“西门庆男宝”后,欲火身上烧,找到娇妻后,说:“小丽,我已今非昔比,弹足粮丰枪更好,披坚执锐要解放你那久攻不下的台湾岛。”娇妻说:“去去去,你土八路能有什么好枪炮?”说来奇怪,他那武器厉害非常,频频向宝岛扫射,顿时硝烟弥漫……
第二天一早,小两口找到尤海轮先生,齐声说:“夫妻合好,全靠西门庆男宝。”
尤先生曾用猴子做过实验,结果发现:猴子服用一个疗程,阴茎增长一寸,增粗两倍。
特别提醒:一,本品仅限家庭内使用,行房时请采取隔音措施;二,不要将本品送给有女部属的男领导干部。
我当时不好立即回绝,说:“容我与老总及有关部门协商一下。”
尤海轮说:“你能登,我给你五万元信息费。”
尤公子走后,我把广告词让老总及编辑们一看,乐得大伙儿笑了个不停。
《烟州晚报》没敢登,一些地方小报和行业报纸纷纷刊登。
尤公子还是烟州城最大的嫖客,一高兴包一层宾馆,哥们弟兄一人一间房一个小姐,尽情地玩吧,我埋单。钱是什么?钱是身上的污垢。
吴传声前几年红得发紫,一幅画能卖两千美金。吴老师仍以画猫和人体为主。他在一幅长卷上画了一百只形形色色、神态各异的猫,听说有位字画商出五十万港币也没买走。
吴老师依旧好色,玩的女人能编一个加强营。
吴老师很爱田苗,女儿却不喜欢她爸,两个人的关系很不融洽。
去年正月初五,我去给吴老师拜年。大画家酒后说自己尝遍了世界各民族女人的滋味儿,就是马上醉死,也无怨言。
也许话里有毒吧,没出半年,他便与世长辞了。听主治大夫说得的是艾滋病。这种病通过性接触或血液进行传播,无药可治,死亡率高。他虽然走了,却给世间留下了五大本画册。吴老的画,已形成一派,号称“吴派”,门徒多达二百余人。
田苗现在是烟州大学最年轻的教授,出了两本美学专著,成了有突出贡献的专家,国家每月给发一百元特殊津贴。她丈夫名叫雷天舒,是烟州公路学院的副教授,有自己的专利。儿子雷相洋已经九岁,小两口一心想让儿子将来能去美国留学。
我曾向田苗求爱,她对我很冷。连碰了几个钉子后,我收了心。
去年春,我问田苗当初为何不接受我的爱。她说:“你的眼角膜是白荷花的,你就是我妈的化身,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。”
王红英正在烟州电影学院表演系上学。演过几部电视剧,但不是主角。
我见过王让一面。他的脸像黄表纸。
再谈谈你的奶奶、父亲和弟弟还有弟媳妇吧。
你奶奶活了九十六岁又两个多月,成为净虚县第一寿星。死前,全身的肉一块一块往下掉,白骨都露出来了。你离开人世那年秋,白鹏翔从沟坡上摔下去殁了,疯疯癫癫的邢竹翠被娘家人接走了。
你的死讯,一直瞒着你奶奶。老人家每天下午都要去村口的皂荚树下等你回来。
你奶奶去世前几年,老傻了,赤身裸体往外跑。
顽童们用土块儿砸她。她边哭边骂:“你砸吧,等我荷花回来,再找你算账。我荷花是县长,有枪哩。一声令下,警车呜呜呜就开来了,把你挂在树上,打成蜂窝。”
什么东西都捡:破纸、烂塑料袋、绳子和柴棒儿,捡回去摞在炕上。
有一次,她把大便拉在塑料袋里,用细绳捆好,说是给荷花熬的钱钱饭。
本不想写这些,怕你心酸,又一想,你让我写信,无非是想知道真实情况,我不能骗你。原谅我,白大姐。
你的事,对你父亲打击太大,没多久,老汉便颅内出血,成了瘫子。坐着轮椅埋完你奶奶回美院不久,你父亲也走了。白老师留下两条遗嘱:一、遗体火化后,骨灰埋在白家老陵;二、书籍、字画和古董归吴田苗。
顺便说一句,你的书籍、字画和古董早已归吴田苗。她现在住三室两厅,满屋子是书,少说有两万册,是烟州市学者中藏书最多的一位。
吴田苗孝敬老人,你奶奶和父亲的保姆都是她出资雇的。
田冬野老师也已离开人世,是病死的,也是穷死累死的。
去年春,我专程去净虚县采访田冬野。田老师患有食道癌。学校交不起住院费,他本人又穷得像一口枯井,只好在家熬中药喝。家中除了满屋子书,没几样值钱的家当。多年来,劣质白酒拼命地喝,旱烟锅子不住地叭哒,头发脱光了,牙是青的,脸是黑的,人弱得一阵儿
风能吹倒。
当时,田老师正写一部名叫《红豆杉》的长篇小说,草稿摞起来有二尺多高。
田大嫂白发满头,一脸忧伤,很少说话。儿子田冬冬患小儿麻痹症,每天摇着轮椅去街头钉鞋。
我谈到你,他没说一句话,两行浊泪流过脸上的道道深沟,滴在破旧的对襟灰袄上。
冯校长对我讲,田老师这些年资助贫困生的钱至少有三万元。
去年中秋,田老师走完人生路。
开追悼会那天,愁云密布,雨滴成帘,秋虫哀鸣。
《红豆杉》的草稿如今保留在省档案馆里,没人去修改,也没人能修改。我大概翻过一遍,给我的印象只有一字:玄。作品以心理感受代替情节,以情绪变化调整文体。全书中的人物没有名字,只有你、我、他、她几个代名词。整个场景似乎发生在梦中,仿佛蒙了一层乳白色的纱。
本不想把这段伤心的文字写给你,但又不能不对你讲。也许你俩在天国已相识,也许已结为夫妻,祝你们美满幸福!
现在人们的思想解放了。书店里放着许多人体摄影册,全裸的特写的都有。笼巷现已改造成书画市场,门面一个接一个,全是仿唐建筑。裸体画到处是:中国的外国的,水粉画油画。
你的画市场上有卖的,标价三千八百元。吴老师看罢说是赝品。
一些女名人纷纷出版自己的写真集,图文并茂,裸体照一张接一张。书店里有的是,一本上百元。烟州某老作家也准备出自己的写真集。这个骚老汉呀,年轻时不出,毛发白了牙掉了,拍什么裸体照呢?浑身松树皮,活蹦乱跳的麻雀变成瘟雀,谁看你呢?我现任《烟州晚报》副总编,主管文艺部和政法部。去年四月二十四日,我和老闻一起坐车来到你的坟前,一页一页撕着烧《阴阳鱼》。一朵朵黑蝴蝶飞向空中,落在迎春花的枝条和柏树叶上。迎春花修长的枝条已把坟堆罩得严严实实。柏树有碗口粗,三层楼房那么高。看完了吗?写得好不好?
如今,科学技术日益发达,不用精卵细胞结合,只需从羊的乳腺细胞里抽出一个细胞来,便可复制出与该羊一模一样的羊来,只是它还需长大。人们称这种无性繁殖为“克隆”。
当年行刑前,科学家如果能从你的身上取一个细胞冷藏至今,你有可能再活一世。唉,做人太累,还是留在天国好,思食得食,念衣得衣,无痛无灾,无忧无虑。
一口气写了这么多,你看累了吧
此祝
春安
程秋杉
二○○○年四月二十四日敬上
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