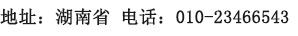入院,彻夜未眠
医院是医院,环境、条件不错。底下几层是各科室,住院区在六楼。病房分单间和套房,大小不一。我选的是小单间,面积不大,倒温馨整洁。有两张床(一张作陪床用)、独立卫浴,好像宾馆标间;靠墙立一只娃娃睡篮,带支架和滚轮,方便推来推去;角落里一架折叠床,上书“护工专用”—医院为每位产妇配备一名母婴护工,即俗称的“月嫂”,负责住院期间的照料事宜。床单上整齐叠放着病号服,上躺一封欢迎函,内容无非“生产顺利”之类,并贴心地赠送了巧克力。床头墙上挂一幅大头娃娃像,光着身子,底下一行醒目小字:母乳是新生儿最好的食物。
我巡视一周,感到满意,连日来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总算撂了地。安顿停当,又跑上跑下做了一堆术前检查。再核对档案、询问病史,接下来是“备皮”—我方才知道并不是“由身上取下一块皮作为手术备用”。最后护士拿来厚厚一摞待签署的文件,大概是“知情同意书”一类的东西;我读得飞快,只知上头啰啰嗦嗦列出许多种危险,随便哪一条都能要命,医院的责任—到底是谁的责任也糊里糊涂;心上发毛,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,和厅长爸双双签了字;护士又嘱咐一遍手术时间,说些早点休息的话,便将我打发了。
我好似母鸡挑拣产蛋的窝一般,踱着步子巡视一周。
厅长爸自陪我进产院,焦虑得不知做什么才好,倒像他要生孩子。我虽面上镇静,却也是生平第一次做手术(医院也没住过),心上难免忐忑。我入了院不生产完毕便不许出去。我们两个各怀心事,又无事可做,只好乘电梯逐层“参观”医院—产房在楼下,楼上是新生儿科,都不准入内;病房入口有个大玻璃间,护士正将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秤,再洗得干干净净;玻璃外面挨挨挤挤一排脑袋,痴痴地望。一想到我很快也将成为那些脑袋中的一个,忍不住唏嘘感动一回。
晚饭前,我爸妈来探过我。我的主刀大夫—便是之前不记得我是谁那位—也来作“术前动员”;我本是自愿开刀,一经“动员”,反倒紧张起来。医院的配餐。规定术前至少六小时禁食禁水,术后也要待“通气”后才能进些流食。要饿上这样久,这一餐我努力吃得很快活。
夜里,我听话早早躺下,当然睡不着,竖起耳朵听外面动静。医院,也住得满满当当。各房的娃娃比赛谁哭得哄亮,好似公鸡打鸣,一整夜此起彼伏,一山还比一山高。不时有人将啼不住的娃娃抱到走廊来回走动拍哄。护士每两小时来听胎心,我便佯睡。肚里那位对于自己几小时后便将到这个世界上来浑然不察,倒比平常还安稳些。我辗转反侧,想着之前与之后的种种,一直到天快亮才勉强打了会盹儿。
术前,身不由己
手术安排在这日八点半。护士约好七点半来接我,我七点不到便起床,换好衣服等。爸妈也赶早来了。我见我妈黑着眼圈,一望便知也是一宿未睡踏实。
接我的人准点来了。我以为是像电视里那样,由推车推我去手术室,不知却是自己走着去。这样好,我也不愿被当作病号看待。一行人陪着我下了楼,到了产房门前,家属便不准进去了—医院允许顺产的产妇家属陪产,剖腹产却不行。我本想说些“别担心”之类的体己话,却没头没脑冒出一句:“我去了。”厅长爸的“欢送辞”是什么?他仿佛是抱了抱我,又或者只是拍拍肩,说了句不痛不痒的“加油”还是“别怕”?总之我既不“英雄”,他也不深情。我自认生命中顶顶重要的一个场合,发生的时候平淡得叫人想不起来。
我随护士走进产房,感到身后的门随即关上了。我没回头,却知道我妈在默然拭泪,又好像看见两个男人一脸的严肃。原来里面还有长长一条走廊,被许多道门分隔成不同区域,手术室在尽头。我走进一道门,门就在我身后关上。我脚下发软,这会倒想哭。感觉走了很久,门开了又关好多回,才终于走到。途中见有陪产的丈夫晕厥,被人架着一摊烂泥似的从产室扶出来。我又想笑,替那女人遗憾。从前听说有陪产的先受不住昏倒,只当是说的人夸大呢。我暗幸剖腹产不让陪,我也不能确定那一位见不见得那样多血腥—还是不知道的好。
进得手术室,眼前明晃晃一片。两三个白大褂正有说有笑地整理器械用品,金属器具碰撞时发出“咣当”声响,在偌大而安静的空间内格外刺耳。室内没个窗户,冷气开得很足。不知是闷的还是冷的—又或者是困的—我一阵目眩,只觉立不住。其中一个白大褂叫我躺到屋中央那张窄床上去。我哆哆嗦嗦爬上床—真是手脚并用地“爬”,那床老高老高—长宽刚好容我仰面躺下。我就躺着,默不作声拿余光四下打量,没人理我。我心里直打鼓,感觉很奇怪,好像小时候转学去了陌生班级,将要上台作自我介绍,又像找工作面试,走进房间,一群面试官等着考我一个;却又不大一样,那时我虽也紧张,好歹成竹在胸,这会我却只有紧张的份儿。
过了好久—也许只有一会,只是我觉得久—刚才那位白大褂过来帮我做“术前准备”。她叫我把裤子褪下,要消毒、插尿管,我照做了。插尿管的过程很不舒服,却并不怎么疼。插好后裤子有没有再穿上,我记不准—彼时许多细节都顾不上,事后也想不起。然后是上留置针。针头比平常输液用的更长更粗,扎在手腕处,拔去针芯,留一截塑料管子。手背上也打上点滴,大概是能量瓶,不教人饿的。头顶输液架挂上好些个袋子,有血,有不知什么液体,一派要“抢救”我的架子。心电图也连上,至此我周身上下遍插管子,躺在那一动不敢动,活脱脱案上猪羊。我越发感觉冷,心上也寒凛凛的,再不以不让陪产为幸了,直希望有人在近旁。仿佛只身在荒原,四下一片昏黑,想喊叫,却发不出声,也知无人能应。我很不争气,又想哭。
最后轮到麻醉—我想要“麻醉”,“醉”了便不必惶然。麻醉师是男的,约莫四十岁,人倒和蔼。他请我背对他侧身,“弓成虾米的样子”。这要求好奇怪,我腆着肚子,又一身累赘,很难做到。他又叫了个人来,一齐帮我变成“虾米”。“放松”,他说。我想着放松,不知怎的却蜷得更紧。腰后一阵尖锐刺痛—比插尿管痛上许多—想是用上药了。他要我“等”,我便等着安然“死”去。过了“好久”,我感到一股又热又麻的劲儿从腰部贯下去,直蔓延到脚趾,便知麻药起效了,可我并未“死”去。我问他,我怎么还没“死”(原话当然不至这般惊悚)?一屋人哄笑。我才知是局麻,“死”不了的,最多“半死不活”。我闹了个大乌龙,又想到要清醒着挨刀,心里叫苦不迭。
麻醉师拿只镊子在我肚子上夹一下,问我疼不疼。我下意识喊“疼”,却不知是否真疼。他又往腿上夹夹,疼—这一次我很确信。他认为要再“等一等”。这时我的主刀医生与人且谈且笑着进来—同她一起为我手术的还有一位,我并不认识。手术马上要开始,我还是不十分确定“疼不疼”—想来多半是紧张的,我可真不争气。麻醉师要我动动脚,我动不了。他便当我“不疼”了。
我晕晕乎乎躺着,神识却无比清楚。腰部以下已被一只“头架”遮挡起来,天花板上的手术灯打开了。灯光晃得我睁不了眼,闭上又要胡思乱想—我生产前那段时期,湖南一孕妇剖腹产死在手术台上的新闻正传得沸沸扬扬—不由自主浑身哆嗦。自怀孕后我常有这样“不由自主”的时候,这令我沮丧。厅长爸不必经历“不由自主”便能做爸爸,我很羡慕。
术中,一世纪的漫长
第一刀下去时,我嘶声叫喊起来。这一嗓子,撕心裂肺,又极突然,竟像别人透过我的胸腔发出的。旁人也许认为我是恐惧,可我真真切切地感到痛。那股痛意立时传遍全身,连骨头缝隙也填满。我喊过之后却再发不出声,只觉意识停滞,脑子一片空白。
我记得麻醉师说要帮我加大剂量,许是我对麻药“不敏感”。我不知道又过去多久,那一刀的刀口是就那样龇牙咧嘴暴露着,还是给掩了一掩。也许我是半昏了过去,因为等我再有印象肚皮已被划开了。我听得我的主刀医生低声对身边的人说:“胎盘有点低。”—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,产检时并未发现“胎盘低”,后来才知低置胎盘难剥离,有大出血的风险。
这时我已不如何觉得痛了,但不痛不代表不难受。痛觉虽消失了,其它感觉还在。我先感到脏腑被牵来扯去,好像要被拽出身体,十分诡异;之后又被强烈挤压,我想象遭车轮碾过也不过如此。巨大的恐怖与不适感将我紧紧攫住。我头皮阵阵发麻,实实在在地感到极度恶心;痛苦得要死,却静静地一声不吭。
我仿佛被车轮碾压了一个世纪那样久,依稀感到两侧又多了人一齐用力压我。不知是谁在说,心跳太快,已近多少次每分—我记不清数值,总之很高。有人又来叫我“放松”,说太紧张对我和宝宝都不妙。其实我不是“紧张”,我是“难过”,“难过”不受我的控制。他们好像给我吸了氧—我也记不清,没人帮我回忆。就在我感到又要昏过去时,我听见刚才的声音在我耳边说:“这下好了,孩子出来了。”这句话轻飘飘的,好似很近,又远得听不真切。
我的小肉团,摄于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。
接下去的事情跟做梦似的,辨不清是真实发生,还是我的想象—也许两者皆有。我先是听见“哇哇”的哭声,极响亮,又急切,好像憋了很久;我是头一次这样近距离听初生儿的啼哭,立刻也跟着簌簌流泪,感到满面是泪。
我看见有人托着一个赤条条的小肉团朝我走来。肉团子有鼻有眼,还很清楚;还长着乌漆漆、毛茸茸的头发;皮肤不似印象中的新生儿那样皱巴巴、红彤彤,虽黏糊着些许未及清理的胎脂及血液,却也瞧得出白净。我只当新生儿都又丑又怪,没想到这一个还挺好看。我觉得神奇,来人问我,男孩女孩?我明明很激动,说出的话却有气无力:“可爱,我的女儿。”我语无伦次,一屋人又笑,却不是讥诮。
那人将我的小肉团贴在我脸旁,要我“打个招呼”。我紧贴着她绒绒的小脑袋,又开始簌簌流泪。我说“你好呀”;她这会已不哭了,却仍然紧闭着眼,不愿搭理我似的。我还未及仔细瞧清她的模样,她便被抱去一旁清理了。
我们母女的初次会面极其短暂。幸好操作台正对我头部,我侧过头便能望见我的女儿。两名护士正麻利地为她消毒脐带、过秤、清洗、穿衣。我分明看见她挥舞着细长的小手小脚,歪着脑袋面对着我,努力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。虽然明知新生宝宝的目力仅限于模糊的物体轮廓,我仍感到她是想要向我这边张望。我和她就那样隔着手术床和操作台之间的一条过道遥遥对视。她安安静静地望着我,我望着她。时间静止,空气凝固。至今我仍清清楚楚记着那画面—那也许是我在生产过程中唯一最清醒的时刻。多年以后也忘不了。
我还痴望着我的女儿,主刀大夫已在为我做下一个手术。不知是麻药未用足剂量,还是药效开始减退—又或是我已筋疲力竭难以忍受—我感到切除囊肿比取出孩子更痛,简直痛得死去活来。麻醉师见我不像虚张声势,问我是否受得住,要不要帮我“睡着”,我急忙喊,要,要。不消片刻我便如愿“睡”了过去—早点让我“睡”多好唷—这以后发生什么,肚子如何被缝上,我如何被推出去,大夫如何将我们母女交还厅长爸,我统统不记得。
我后来才知女儿一直孤零零地被放在操作台上,直到手术结束才和我一起被送出来;我胎盘低,囊肿又大,手术难度超出预计,本来45分钟便可完成的剖腹产手术,足足做了两个半小时;羊水抽走后胎头久娩不出—便是我感到被反复“碾压”时—一时胎儿有窒息可能,但总算有惊无险。主刀大夫对厅长爸报出“母女平安”时,他正因久未见我出来焦灼不已,坐立不宁,据说他立时“热泪盈眶”。这些都是我醒来后家人说与我听的。
“他们为什么不先把宝宝送出来?”我却只关心这件事。“宝宝好可怜,生下来便没着没落,自己呆了那么久。”我反反复复叨念着,始终意难平。
我平安出了手术室,还做了妈。女儿出生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,上午八点五十六分。
术后,更难的在后头
我醒来已回到病房,躺在自己的床上。身上盖着厚棉被,插着尿管,吊着镇痛泵和能量瓶。好奇怪,我还是一动不能动。麻药劲头已褪去大半,镇痛泵效果不明显,刀口痛第一时间袭来—我几乎以为我是痛醒的—我未及开口说话,先痛得眼泪流下来。我妈正对着我床边睡篮里的小宝宝说话呢,见我醒了,急忙凑上来。又看我痛,也跟着簌簌流泪。
护工这时将宝宝抱来吃我。我不能侧身,她便趴在我胸前,很努力地吃。我已有了初乳,只是很少。我不忘嘱咐护工只许喂水,不准喂奶粉。我头很重,无力醒太久,又昏昏地睡。睡一会又醒,如逢宝宝恰巧也醒着,护工便再抱她来吃。
有时我被迫醒来,因为护士每两小时要来帮我“压肚子”—即按压宫底,旨在帮助宫缩,排出恶露。这一关是我认为最要命的—比手术过程还叫人痛不欲生。按的位置正好在刀口以上;每按一下,我只觉灵魂出窍,一手死命抓紧床栏,一手直将厅长爸的手掐出血印子来。我挣得一身冷汗,又不敢喊叫,叫了喊了想必更痛,大气也没法出,面目怕也是狰狞的。每次要按四、五下肚子,那一天大概按了四、五次。“生不如死。”我只剩得一口气,哭丧着脸对厅长爸形容。
我生产完的当晚,我妈胆结石复发,医院,第二天便动了手术。我们母女约好似的开刀、住院,我爸需服侍我妈,顾不得我,我身旁只剩下厅长爸和仅相处了半日的护工。我一方面牵心挂肠,一方面没了我妈照顾,一下子像失了主心骨,更感到术后日子难捱。我妈也放不下女儿及刚出世的小孙孙,病中叫人接了我二姨来管我几日。我后来才知,我原本订好的月嫂竟也在同一天因急病入院,我不愿认为老天爷故意要我为难,但连串“巧合”,确令我惊诧又无助。
我一次做两个手术,失血比一般剖腹产多,伤口也长,恢复得格外吃力。术后第二天拆了尿管,要求尽早下床活动,可我压根直不起腰,每迈一步便感到伤口要炸开,走不了两步便满头大汗,只能坐在床沿喘粗气。第三天摘了镇痛泵,护工担忧我受不住,但我嫌它碍事,执意要摘,不料想本已缓解的刀口痛又卷土重来,我又倔,只好死要面子活受罪。第五天,我二姨去相邻病房“考察”一周,回来后笑我,对面和我同一日剖腹产的,已自己抱起小孩走着出院,我却连走去厕所都难。
这是事实。前几日我大小便都只在床上,又害臊不要旁人看见,厅长爸像服侍老病得走不了的老伴一般,拙手笨脚为我把屎把尿—真难为他。夜里起来,不忍拂醒他人,咬着牙、掐着腰自己挪去厕所;好容易在马桶上坐定,却不敢用力,憋红了脸也没上成,又灰溜溜挪回来—真正是“扶墙进,扶墙出”。后来出院,我也没能“走着”出去,全靠轮椅推—我到底坐上轮椅了。
术后哺乳也比自然产困难许多。为免宝宝压迫伤口,勉强能翻身后,我便侧卧喂她。她每吸吮一次,我便明显感到宫缩一次。宫缩虽不及“压肚子”痛,却也比痛经痛上好几倍。剖腹产奶水来得慢,她每次需吃上好久,我便咬牙忍耐好久。她饱足了,我已浑身汗透,几近虚脱。
前两日我奶水少,胸前软软。来探望的人问起,护工便替我回答:“她没有奶。”我一不喜欢有人着急来探,因为我蓬头垢面,又只想睡觉;二不喜欢护工替我回答,她怎知我有奶没奶?即便没有,我也不愿她四处说与人听。我虽是无力产妇一位,却也有脾性,也有傲骨,也有我的小心思。我做了妈,骨子里还是女孩。这位护工哪里都好,就是嘴快。
我很争气。第二天夜里,奶水急汹汹地来了,胸前一下子涨成两个硬邦邦的石头,连胳膊也抬不起来。宝宝吃了半天,仍不见软;我二姨和护工把我架起来,一人一边帮我按摩,又用吸奶器吸了半天,只吸出二十毫升。“管子堵的。”护工很笃定,隔日一早便帮我叫了通乳师来“开奶”。“开奶”顾名思义,便是要把乳房里大大小小的奶结硬块硬生生用手揉开,真正“享受”。我只当喂奶便是“我喂她吃”,不料想竟这般“折磨”,直呼“我不喂了”,没人理我。大家都认为我必须喂。我没得选择,忿忿不平,却也一口气喂到了如今。
至此我已将各种痛法身经个遍,再不敢认为剖腹产“不痛”了。若有人问我“痛得值不值”,我只当这人思路不清。好像“痛”由得人选择,并且很值得歌颂。在我看来,痛便痛了,还要被冠上一顶“伟大”的高帽,简直是极不人道的。我见过一位女作家形容分娩痛:“就像被挂在酷刑架上,你不会想当英雄的,你只会卑微丑陋地喊苦,我什么都招了”,我觉得很恰当。我身旁确有不少人—包括女人自己—坚持认为生育之痛(特指自然分娩)是女性须得承受的,除去技术因素,这或可部分解释为何无痛分娩(也称分娩镇痛)在国内迟迟获不得普及。我生产的医院在推广无痛,据说接受率也不高。
我不愿深究这种讴歌苦难的价值观是如何形成,又或我能够明白,却不便撼动。只不过对于身旁戚友,我从不“鼓励”她们去承受生产之苦,或为之拍手称勇。我只愿她们少受些苦。这样的苦,或许将在她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画上过于浓墨重彩的一笔,令她们很难真正轻松、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新角色。
一段小插曲
第三天上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。宝宝被测出“黄疸过高”,护士让照蓝光。我认为宝宝并不很“黄”,白着呢,她是危言耸听,不愿照,她便三番两次来催,将情况说得很严重。我记得我斜靠在床上,既气愤又无力,诘问她:“你怎么唬产妇呢?”她比我老练,漠无表情,叫我“后果自负”。我们两个新爸新妈只怕误了宝宝,硬着头皮将宝宝“送”与她。
照蓝光在楼上。开始说好照十二小时,又延长至二十四小时。我二十四小时见不着宝宝,躲被子里嘤嘤地哭。厅长爸发现了,便每两小时上楼,拍了她的照片来给我瞧。我见她被剥个精光,一个人躺保温箱,哭得更止不住。厅长爸哄我她这时还像小动物,不需人陪;这话仿佛奏效。后来才醒悟过来是谬论。
出生后第三天,因新生儿黄疸住进保温箱。
我不能亲自喂她,便将母乳吸出,由厅长爸送上去交给护士。我拜托他们别用奶瓶,用勺子喂,还是没人理我。我费了半天劲,挤出三四十毫升黄灿灿的珍贵初乳送上去,人家早用奶瓶喂上奶粉了,一气喂了六十毫升。“她喝得咕嘟咕嘟的”,厅长爸对我形容。我白受了吸奶的痛(吸奶器也会刺激宫缩),心上也痛。
我们母女分别二十四小时,回来后宝宝便“乳头混淆”,认了奶瓶作娘了。她小小一只居然辨得明白,这妈(奶瓶)好吃,那妈(我)不好吃。我不肯放弃,不吃便饿着。她比我还倔,宁可饿着也不从。她哭我也哭,大家都说,娘儿俩真像。我又吸出来,叫人用勺子喂她,喂得又慢,洒得又多。胎粪也少,胆红素排不出,眼瞧着又“黄”了许多。无奈只好又喂奶粉。我奶水本已多起来,她不吃,又堵了回去。
我本无意执着于母乳,这一来反倒激发了我的“斗志”。此后我每次必先亲喂。她有时吃,有时不吃,我便三小时(不分昼夜)吸一次奶,以保证泌乳量。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出了月子,我才实现纯母乳;又继续以瓶喂为主、亲喂为辅近四个月后,她才终于彻底接受亲喂。如今回想,我仿佛是着了魔。可女儿本来吃得很好,产后母婴分离可能直接导致母乳喂养失败,我读过指导书籍,却想不起来,也从无人告诉我。我想起床头墙上那句“母乳是新生儿最好的食物”,只觉讽刺。
这虽是一段小插曲,却令我初为人母的路走得异常艰辛。我刚做了妈,有许多惶恐。好像受了不少“指导”,却仍不知该如何做。我喂不得,不喂也不得,进退两难。即使我自己拿主意、想办法,豁出去半条命,总算“成功”,后来也尝到母乳喂养的种种好处,我还是不能确定旁人该为我骄傲,还是笑我执拗?至于我自己,我是有点糊涂地做了妈,又有点糊涂地将宝宝母乳到了满地跑;我深深领教了“难得糊涂”。
生命是怎样一回事
医院住满七日才回家,一个月后方能行动自如;我是疤痕体质,半年后剖腹产伤口仍偶尔发炎,两年后刀口处留下一道凸起的暗红色淤痕。我并不在意,将它视作身体一部分。女儿好奇发问,我便告诉她她由这里来到世界上,“像滑滑梯那样”,我说,她很开心。
女儿作为小生命“破壳”了,我作为母亲也“破壳”了。这也是我的新生,它令我从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生命。我也曾自问,如果不做妈妈,我的人生是否有更多可能—那些被认为更“好”的可能?而我始终肯定,人的生命获得深度,并不因为去做什么和不去做什么,而在于我们如何定义与承担发生在生命里的每一件事。
我如实而坦诚地记下女儿“破壳”的过程,不是想告诉她我是母亲,你是我的孩子,而是邀她来看一看,生命是怎样一回事;她的到来于我而言,并非文化、习俗和惯例所希望母亲向她的儿女宣称的那样,源自某种成熟、完美而无可争议的决定,而是如同生活中的其它一切事件,挟带着偶然、懵懂、创痛、困顿;令她认识这一份深刻关系的真相,并且看见妈妈在其中如何挣扎、探究、建设、努力,是对她、对自己,也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。
我愿她由此理解,妈妈是怎样一个人;我和她,是紧紧相连又各自独立的生命,而不是,我孕育了你,你须担起我。
这其实是很孤独的一件事。是的,怀孕、生产、养育,自我的粉碎与重塑,为人母的每一步,都是彻彻底底的孤独。可哪件事又不是呢?人之孤独处境,并不因选择而不同。惟其如此,才能够不顾一切往前走;走下去,便能抵达清明之境。
作者:陌上依依,传媒硕士,互联网从业者,天蝎座,家有两岁狮子座女宝宝一枚(此处大量留白),育儿路上痛并快乐,屎尿屁里摸爬滚打,长存赤子心。
-Miss不要-
分享育儿这件浪漫的小事
这是我的第13篇原创文章
长按2秒即扫码订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