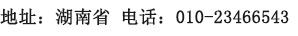俞妍,浙江作协会员,浙江省第三批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。年开始练习小说,自由投稿,有短篇小说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清明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朔方》《山东文学》《雨花》《小说林》《黄河文学》《青岛文学》《短篇小说(原创版)》《翠苑》《文学港》等刊物,约35万字。曾参加首届鲁迅文学院浙江高级作家研修班,首届鲁迅文学院河南高级作家研修班,陕西作协中青年作家(陕北片区)培训班。已出版短篇小说集《青烟》《蜗牛》。
1
那个女人进来时,潘鹤鸣正翻着行李袋。女人说,她是阿央介绍的,阿姐还没出来吗。潘鹤鸣嗡着鼻子嗯了一声。他不知道阿央是谁,女人所说的阿姐大概就指雪娣吧。
女人放下自己的东西,开始整理病床和床头柜的杂物,手脚很麻利。潘鹤鸣瞥了她一眼,自顾扬着手掌,看上面的裂纹。他的手掌在日光里泛出玉样的色泽。从中午开始,潘鹤鸣已经无数次看自己的手掌了。正中的那根线横穿手掌,像是要将手掌割裂。
雪娣是十点推进去的。推进去的时候,外面有她母亲,大姐,二姐。三个女人等雪娣推进手术室后,回到病房,叽里呱啦叙说雪娣的种种辛苦。她们说的是本地话,但潘鹤鸣听出每一句话的矛头都指向他。她们以为他听不懂,或者她们知道他能听懂却故意说给他听。他坐在折叠后的躺椅上,低头划手机,等实在听不下去了,起身出门到走廊里兜了几圈。
走廊靠近护士站吧台的墙壁上,挂着电子屏幕。上面显示的正是该科病人上手术台的消息。“宋雪娣……正在手术。”看到这条,潘鹤鸣哆嗦了一下。他回转身,看见一个护士拎着一袋盐水走向某个病房,尿黄色的盐水让他小腹微微胀痛。他往回走,推开病房的门。里面的三个女人见他进来,停止了说话。
不知过了多久,护士领着一位医生走进来。那位自称童医生的男子问谁是家属,三个女人围上去。童医生说病人情况不大好……他低沉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,嗡嗡作响。潘鹤鸣盯着他的下巴,上面的胡楂像密集的小黑点在不断晃动。最先哭出声的,是雪娣的大姐。她捂着嘴,一屁股坐倒在病床上。随即,二姐也叫了一声老三,像一口气接不上来。
这个要家属签字。童医生举着水笔问。雪娣的母亲冲上去说,我来签。潘鹤鸣感觉到童医生的目光,艰难地说道,我是她丈夫。童医生递笔给他说,这个要你签。潘鹤鸣拿起笔签上名字。
童医生出去了。岳母对着门吼了一声,凭什么我不能签,我是她亲娘呀。她拍着床单哀号起来。我的老三呀……
潘鹤鸣跟了出去,他已听不到背后那群女人的哭声。潘鹤鸣问童医生雪娣还可以熬多久,童医生叹了一声道,少则三个月,多则半年,当然能撑到一年的也不是没有。
大哥,您也不要太难过。女人整理完,又灌来两瓶热水。她问潘鹤鸣雪娣是什么时候推进手术室的。潘鹤鸣说中午十一点。她哦了一声,轻声道,大哥,咱活着,全靠命……潘鹤鸣没应声,对着日光慢慢仰起脸。
2雪娣推出来,已是下午四点。病房里来了更多人。除了把雪娣搬上床,潘鹤鸣基本搭不上手。医生嘱咐着,头六个小时麻醉还没过,千万不能让她睡过去。那些人嘤嘤嗡嗡嚷着,只有护理的女人拿棉签沾湿了在雪娣嘴唇上涂。医生提醒他们别都围着,影响病人休息。大家才陆续散去。
天色渐渐暗去,病房里剩下雪娣的母亲、大姐,还有雪娣的儿子晓敏——他在省城出差,刚赶回来。潘鹤鸣买了快餐,大家聚着吃了些,商量着谁留下来陪夜。晓敏说,外婆身子不好,大姨家里有事,都不适合陪夜。叔叔呢,也累了,今天还是早点回去休息。晓敏很少说话,一开口却是一套套的。跟小时候一样,他一直叫他叔叔,此时听来,声音却像变了调。潘鹤鸣不吭声,两个女人看了看潘鹤鸣,也没有反对。病房里寂静下来,只听到氧气灌里的管子口在咕噜咕噜冒着泡。
一个护士走进来,给雪娣换了一袋抱枕大的盐水,是那种讨厌的尿黄色。潘鹤鸣拨了拨盐水管子说,我睡不着,还是让我陪吧。晓敏犹豫了一下,也答应了。他说老妈住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,后面的日子长着呢。他起身扶他外婆。雪娣的母亲和大姐又开始用当地话絮叨,她们说得很轻,大概怕被雪娣听见。潘鹤鸣坐在旁边,觉得自己像个贼。
他们走了。潘鹤鸣像在水里很疲惫地游了一圈,爬上岸。护理的女人凑近雪娣耳边说话,却听不出她在说什么。几分钟后,见雪娣还没反应,她就提高声音。大姐,您在听吗。雪娣眨眨眼皮,她就放心了。她放下棉签,从一个纸袋里掏出一个橘子,很小心地剥开皮,将里面的肉取出来,掰了一半递给潘鹤鸣。潘鹤鸣捏在手里,一根根抽橘瓣上的细丝。女人也没有吃橘子。她把橘皮摊在手心里,拿了一小截短蜡烛点燃,用烛油粘住橘子皮的底部,又用针线缝住分叉的橘皮上端。完工后,女人把橘皮拎起来,问潘鹤鸣像不像一盏灯。潘鹤鸣眼前一亮,碰了碰橘子皮说,真好看。女人又拎起橘皮在雪娣眼前晃荡。大姐,您能看到吗。雪娣勉力睁开眼,又合上了。
时间已过九点。邻床的大妈早已入睡,鼾声响得像沸腾的高压锅。她是昨日做的腹腔镜手术,今天已能下床了。她女儿昨晚伺候了一夜,也倒头睡去。房间里特别安静,潘鹤鸣撑不住了,将头埋在膝盖里。
大哥,您也回去吧。女人轻推了他一把。潘鹤鸣抬起头,恍惚了一下,像呆在虚空里。女人说,六个小时的麻醉期很快过去了,接下来就没事了。潘鹤鸣揉揉眼睛,看见女人的马尾辫很清爽,裸露的耳垂温润如玉。你叫什么名字?他冲口道。其实刚进来时,她已经自我介绍过了。哦,阿莲。他想起来了。她含笑点点头,光洁的额头上,一条笔直的皱纹像一枚针在眉心间轻轻漾动。
3这样的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梦里,他年纪还很小,捧着一个空碗走在狭长的胡同里。胡同很暗,墙壁上爬满发黑的青苔。好像刚下过雨,青石板泛出一个个黑圆点。他捧着碗摇摇晃晃地走着。一个毛茸茸的东西突然出现在身后。回头一看,一只狼一样的怪物,正龇牙咧嘴盯着他。他尖叫着跌倒了,碗摔在地上。此刻,黑漆漆的胡同闪出一道白光,一个女人出现在眼前,身上扎满了碎瓷片,浑身是血。我不是故意的,不是故意的……
潘鹤鸣醒了,没开灯就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。他用手机的光探照右手掌上的裂缝。那条裂缝跟梦里的怪物一样青面獠牙。他担心旁边的雪娣醒来,将手机放进被窝,对着右手仔细照,好像手机是照妖镜,能把当年的一幕照出来。
母亲曾多次给他说起断纹的来历。说他四岁时,和邻居三丫头一起去她奶奶家讨菱角吃,不想胡同里蹿出一只狗,吓得他摔破碗,右掌扣在碎碗口上……这件事,他一点记忆都没有。比他大一岁的三丫头倒记得很清楚,说当时看着满地的血,她吓哭了。三丫头后来做了他的媳妇。他们的父母都在钢铁厂上班,他和三丫头青梅竹马,同班读书到高中,结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